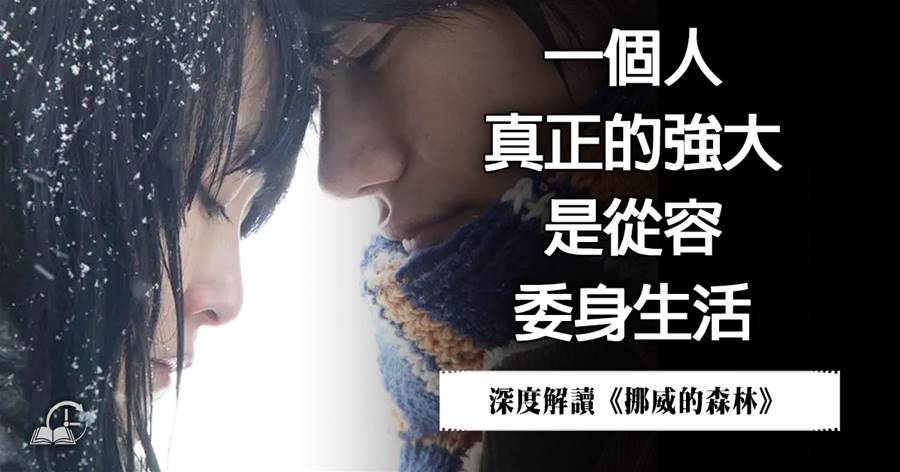

1986年,已經37歲的村上春樹,決定寫一部關于青春的小說。
于是,他拾起記憶的殘片,以一個成年人的視角,重新拼湊了一段純真又放蕩、彷徨又堅定的青春,也就是1987年問世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。
幾十年來,關于這本書的評論,眾說紛紜,褒貶不一。
有人認為,這是「青春傷痛文學」的代表作;也有人認為,這本書過于露骨。
可是,對于陪跑諾貝爾獎十幾年的作者本人村上春樹來說,這卻是一部「百分之百的現實小說」,是他一生僅有一次的「成功之作」。
20歲時讀《挪威的森林》,只感受到少男少女們,被困在青春那片霧靄叢林里的感傷。
30歲再讀這本書,讀到的卻是主人公渡邊,由一個懵懂男孩蛻變、成熟,最后適應生活的過程。
這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,更是一部成長史詩。


成長,從失去開始
木月,是渡邊高中唯一的好朋友。
在渡邊看來,木月頭腦敏銳、談吐瀟灑,具備一種讓人感到舒適的魔力,他總能把不合群的人拽入談話。
可如此耀眼的木月,卻在高二那年,在拉著渡邊逃課打了一下午桌球后,于當天夜里自盡了。
沒有預兆,也沒人知道為什麼。
這是渡邊第一次真切地感受死亡和失去,此后很長一段時間,他都無法確定自己在周圍世界的位置。
一年后,渡邊在電車上,與木月的女友直子偶遇。
一個失去了唯一的朋友,一個失去了青梅竹馬的戀人,兩人因有著同樣的痛苦越走越近。渡邊對直子漸生情愫,而直子也希望,通過渡邊開始全新的生活。
20歲生日那天,直子不顧一切把自己交給渡邊。而仍然愛著木月的她,又從心理上無法接受這種行為。
精神與肉體的割裂,促使直子徹底崩潰患病,休學住進療養院。
無法相見的日子里,渡邊以紙傳情,訴說思念。無論等多久,無論直子還能否痊愈,渡邊都希望可以一直陪著她。
後來,渡邊從宿舍搬出來另租住處,他希望能與直子一起生活,以便照顧她。
年少時的情感,沒有現實的羈絆,也沒有世俗的偏見,只純粹地追求天長地久。
然而,就在他滿懷希望地等待跟心愛的女孩開啟新生活時,直子在療養院自盡了。
人生才剛剛開始,渡邊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最愛的女孩。
書中說:「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時代,居然凡事都以死為中心旋轉不休。」
死亡,或許不是成長的主旋律,但失去一定是。
曾以為,成長就是日子一天一天地過,後來才明白,在我們體會到失去的那一刻,成長才真正開始。
也許,是在發覺父母變老的一個瞬間,你知道自己從此將失去庇護;
也許,是在面對某些選擇時,你意識到自己力量有限,被迫妥協放棄;
也許,你只是簡單地犯了一個錯誤,卻不得不承擔后果。
那一瞬間,你感受到來自生活的重量,開始掙扎著,渴望變得強大。


比前路未知更可怕的,是試圖掌控命運
木月的死,使渡邊前所未有地體會到人生無常,并陷入了無邊的迷茫中。
他開始放縱自己,想從中得到某種解脫,卻又每每因此變得更加空虛寂寞。
渡邊正常讀書、與人相處,卻又在心里與所有人保持距離。與直子重逢前,他的心不向任何人敞開。
有些東西,如果要不可控制地失去,倒不如從一開始就敬而遠之,以免失望。
然而,如書中所寫:「當你是個陌生人的時候,這個世界對你就是陌生的。」
他越是試圖以這種方式掌控命運,就越孤獨,也越來越邊緣化,渡邊變得更加不知所措了。
直到直子決絕而去,另一個女孩,不由分說地闖入他極力封閉的心。
在學校旁的一家小餐館,渡邊與綠子因一本筆記結緣。
坦率熱情的綠子毫不掩飾自己的愛意,一步步主動向他靠近。
他們在一起時,總是一個不停地說著,一個安靜地聽著。
一來二去,渡邊對綠子有了一些了解。
綠子的生活更為不易,可她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學。在綠子看來,人生就是一個餅干罐:
「餅干罐裝有各種各樣的餅干,喜歡的和不大喜歡的都在里面。如果先一個勁兒地挑喜歡的吃,那麼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歡的。
「每次遇到麻煩我總這樣想:先把這個應付過去,往下就好辦了。」
綠子跟渡邊一樣,也在與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抗爭,只是方式不同。
在綠子身上,渡邊發現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。
周國平說:「人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,但可以支配自己對命運的態度,平靜地承受落在自己頭上不可避免的遭遇。」
生活中很多事情的發生和走向,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。
因為經歷過失去,見證過不幸,我們總是太急于將生活納入自己的軌道。殊不知,越是如此,就活得越擰巴。
人生無常,沒有人能完全掌控它,我們唯一能做的,就是改變面對它的態度。


一個人真正的強大,是從容委身生活
直子連接的是渡邊純真的少年時代,而渡邊通過綠子看到的,卻是雞零狗碎的現實生活。
綠子雖有相親相愛的父母,她卻并未得到足夠的愛。在父母面前,她甚至連撒嬌的權力都沒有。
綠子的母親在她讀高中時患病。綠子從十幾歲起就一邊上學,一邊打工,平時還要與姐姐一起照顧母親。
母親去世,悲痛欲絕的父親竟然希望綠子姐妹,能代替母親去死。
本就沒得到過多少家庭溫暖,綠子那點可憐的感情早已被傷得支離破碎,可日子還得往下過。
兩年后,綠子父親因腦腫瘤住院。綠子每周有4天要在醫院看護,面對父親的醫療費,她甚至不確定自己能不能讀完大學。
時而遇到來探病的親戚,還會嘲笑她吃得多,父親病成那樣,女兒竟然還有心情吃飯。
父親過世后,綠子說: 「過去太殘酷了,往后要狠狠撈回來。」
生活一次次重拳出擊,綠子都從容化解,并因此練就了強大的內心和堅韌的品性,這不僅幫助她跋涉出了人生的泥沼,也救贖了她心愛的男孩。
渡邊告訴綠子:「見到你,我多少適應了這個世界。」
或許,我們都曾同渡邊一樣,向往諸事圓滿、萬事順遂的夢境。可是,生老病死、穿衣吃飯、一地雞毛的現實,才是生命最真實的載體。
過了做夢的年齡,人就得接地氣兒地活著了。
就像黑塞在《悉達多》中寫道:
「我不再將這個世界與我所期待的,塑造的圓滿世界比照,而是接受這個世界,愛它,屬于它。」
真正的強者,不是龜縮在自己的世界里造夢,而是能夠從容委身生活,是面對衣食住行、柴米油鹽的瑣碎,依然保持熱情。


村上春樹在書中寫道:「即便再竭盡全力,該受傷害的人也無由幸免。」
人這一生,得失榮辱、聚散無常,不在這里跌倒,也會在那里受傷。越是用力想避開,就越是會迷失自己。
曾幾何時,我們不敢結婚,怕所托非人;不敢生子,怕生活方式被重構。
可是,生活的磋磨,并未因我們逃避選擇而有所收斂。
下班回家后的冷鍋冷灶、夜深人靜時的孤獨落寞,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:生活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。
雖然,并非人生中的每次選擇都正確,但比規避風險更重要的,是經歷的豐富和生命的充實。
有糾葛,才有故事;有開始,才有結局;所有失去,都是為了以另一種方式歸來。
不去經歷,又怎知是否值得。
春有碧草,秋有落花,時光清淺,慢渡日常,我只愿你別辜負了自己。